普羅米修斯情結
在《火的心理分析》一書中,巴舍拉(G.Bachelard)說火是一個單調卻又閃動的現象,它包含了一切,它說話,它飛舞,並且對著你歌唱。這是屋內火爐那種被馴服的溫暖,它總是充滿情感的記憶的。誠如藝術家羅森豪所說的,在拉坯動作中的無聊與單調終會轉化成內心自然明淨的專注,直到無聊變得強韌而有力,一種同語反覆(tautologie)在徹底與絕對中達到的美感,如斯多葛般苦行修練的苦後回甘與純真。然而火也是節慶,是再生!巴舍拉也提到:「普羅米修斯情結就是知識生活層次的伊底帕斯情結。」如果說藝術家羅森豪對土(地)的感知與熱情是現象學式的,那麼它對火的知覺就比較是語言學的狀態。
羅森豪對藝術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式觀點提出批判。此理論提出,社會做為藝術的載體同時也是生活的文本與場域,是故生活為藝術的源頭,社會及其制度規範著藝術的創作產出—這是一種決定論式的藝術詮釋模式,而羅森豪的主張卻是較為積極並且主動的—藝術家羅森豪將錯綜複雜的社會結構視為藝術的工具與方法,以開創的觀念將藝術視為社會發展的「發電機」,如此社會的內容才有變化與提升的可能。(《樂土p.28》他也因此認同波伊斯(Joseph Beuys)的「社會雕塑」理論與「擴展的藝術觀」概念,將社會視為一件雕塑品,以藝術的行動機及實踐藝術運動來進行社會的改造,深具歐洲知識份子介入社會的理想特質。)
此時,當羅森豪展現普羅米修斯情結的強烈火熱而且充滿熱情,刺痛社會,要世界翻過來,近乎宗教情懷式的激情(passion),滿懷著受難殉道的積極意願並且親身實踐。然而火可以收縮又可以是膨脹的,它拆散可是它又聚合。(Le feu est aussi bien le principe de contraction que le principe de dilatation, il disperse et cohere.)
「聲音與憤怒」的火
羅森豪在重返原鄉的自述中,曾經對台灣的藝術史進行一個歷時性也是歷史性的反省與覺醒。
九零年代之前,台灣的藝術史似乎永遠是某種橫向嫁接的邊關稗史。在八零年代的開放與自省醞釀之下,九零年代的台灣就像初獲解放的暴發戶,因自由的吶喊而激動得顫抖,也像是一個澎湃的辦桌席,政治革命與文化藝術革命同時激昂的如煙火綻放。李登輝上台解放了台灣自主思考勇氣與行動能力。八零年代紛紛設立的藝術學校與科系,增加了大量投入藝術場域的創作者。冷戰結束改變了世界的思考方式,一切都變得可能,全球化的文化產業進入台灣產生強大的衝擊,社區營造與野百合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藝術節;小劇場、公共藝術、社區營造、另類空間、地下音樂等百花齊放、萬紫映千紅。羅森豪的藝術行動無疑是其中最動人的風景之一!他直接參與帶動了台灣新文化建構的過程。在風馳電掣的聲音與憤怒之後,藝術家進而進入教育體系持續其革命的熱情。
在二零零二年德國史坦堡的作品「國王的禮物」,以及隔年羅森豪代表亞洲參與德國羅特威爾的當代藝術論壇之後,其創作已經進入了另一種境界,對土地的熱情近乎無限上綱的還原與擴張。二零零四年的「氣味相投」是他創作風格與形式的一個重要轉折,企圖打抱不平的憤怒漸漸平息了,回到底層的記憶,回到生命原初的美好,讓熱情進一步提升的羅森豪出現了。
在風與火之外,土與水的包容特質,陰性成分更具體的在其作品中進場展現。「本土」從一個抽象與理想的政治概念,轉化成一個具體的身體感的生命經驗概念,回到以土地為本的本土的積極性概念源頭。
事實上九零年代的聲音與憤怒的種種激情,讓抗爭對象的執政者慢慢學得了更靈巧的應對技巧。特別是理想性的藝術介入行動,逐漸被政治所熟悉收編成制式化的文化政策,而革命式的語言也在各種形式的誘惑之下,轉化成花俏浮誇、虛假矯揉的後設論述語彙。藝術介入行動於是轉變成以藝術之名的政治,美學就變得次要而且虛假,在政治符號操弄下,藝術的本質漸次被掏空乃至消失殆盡了。
洞悉所有的活動與事件終究在成住壞空之中輪迴,藝術家的自主性思辯與創造能量促使羅森豪回歸土地,大自然中豁達自在的感動開始充滿了他接下來的天目創作。
part3待續...
Anadou木作創作展
8 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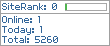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