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陳泓易(南藝大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助理教授)
生命動力(procreativite)或藝術的創造力(creativite)
歐洲對「文化」(culture)的定義一開始是與土地息息相關,這個字源自拉丁文的cultura,指的是人對於土地的耕耘,與農業(agriculture)同一字根;後來轉化成某種智性訓練,期以促進性靈質地與功能的發展。
古羅馬哲學家西賽羅(Cicero)與啟蒙時期的思想家把它當作是一種對個人或着社會整體的一種教養,藉由文化的教養,個人得以變成更完善的人,社會得以進化提升。這與自然一樣是一種結合土地作為隱喻的概念與實踐。
在自述性的詮釋書籍《樂土》當中,藝術家羅森豪以此作為個人重返原鄉的啟示,也簡單概括了其藝術創作某種可見與不可見的主軸。「土」—不僅是他創作最主要具體的材料,同時也是他創作概念的中心、身體與心理的樂園,以及其抽象隱喻的根源。從一塊泥土到整個土地大自然,甚至蒼穹宇宙的昇華,他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往前邁進。而火一直是他的媒介,爐灶的火、燒陶窯裡的火、對社會的熱情與憤怒的火,他總是鑽研照亮追溯到最深層的本質去呈現或突顯事物最初的真實。
從燒陶到藝術的社會介入再到天目的創作,羅森豪總能回到本質去孕育,去創造。其藝術不同於一般的創造(creation),是一種具有土地母體式的生命動能(procreation),所成就的每一件作品都有土地所孕育轉化的哲學深思的意義。
現代性與先驗
工業革命帶來了現代化,卻也由於都會化讓人脫離了土地的緊密連結,而現代性改變了藝術的形式也轉移了美學的思辨邏輯。笛卡兒(R.Descarees)的解析幾何提供了康德(I.Jant)先驗(transcendance)哲學的基礎,現代性創造了先驗的(transcendant)認識論也創造了「非親身」(disembodied)的藝術形式,使得藝術逐漸脫離本質,變成概念,變得抽象(abstract)。當代對現代性反省的哲學家認為,現代性的過程不過是純粹化(idealisation)與客體化(objectivisation)的過程。純粹化是科學思想的產物,身體的知覺與溝通永遠都是多層次並且複雜的,身體的知覺傾向詩的語言。
而將人拔離餘土地的西方現代性,也併發了嚴重的非預期共伴效應(variation concomitante)的社會病徵,波及到每一個現代化都會中的個人,馬克思(K.Marx)將此稱為「異化」(alienation),而心理分析家佛洛依德(S.Freud)則稱之為「unheimliche」,一種莫名的陌生的焦慮。從現代藝術到前衛藝術,西方一直試圖處理卻從未真正解決這一個現代化的基本命題與難題;台灣接受西方的藝術形式的橫向移植與嫁接,在這樣的情境下更顯得荒謬。
在作品中處理了「原鄉」(heimat)與「它鄉」(fremde)的問題後,羅森豪碰觸到了unheimliche問題的核心,於是對台灣的文化藝術問題提出他的看法:「沒有根與主體意識的認知,要奢談文化與藝術,就如同自我欺騙一般!」heimat這個自同時也指涉了「認同」與「主體性」的概念,羅森豪以此進一步擴張並說明創作實踐的過程:「不過是為了成為自然的一部分。」
我們於是可以漸漸明晰,「土」的概念與材料如何形成藝術家創作的主軸。以土為素材,羅森豪在非親身的藝術與親身的(embodied)的藝術之間辯證,親身的藝術形式是具有濃烈身體感的,是無法被純粹化與客體化呈現的。感官知覺的認識論從來不是線性純粹的,它永遠是多重面向與多重層次交錯綻放的。
藝術總是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交錯呈現,藝術家一如魔術師創造幻象(fantasmagories),讓不可見變得可見,而抽象的藝術卻讓不可見替代可見。也就是說,某種程度讓影像逐漸變成了符號。或者說,在當代藝術中,太多時候概念凌駕甚至抹滅了藝術,當代藝術變成一種非親身的行為或者觀念,如此也讓藝術中原先的許多美好消逝殆盡。許多時候藝術在與政治抗衡的同時,也變成了另外一種形式的政治。
part2待續...
Anadou木作創作展
8 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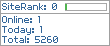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