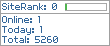藝術家的天目
羅森豪回到生命中最原初的美好,以天目書寫火與自然的詩篇。每一個天目碗都是火與這塊土地的自然泥土交響的詩篇,有華格納歌劇的壯闊,也有蕭邦夜曲般的華麗;有北管的喧囂,也有南管的細膩與抒情。他彷彿具有巫師與魔法師的通向靈異的能力,讓常人不可見的世界一一在他跟前現形,解讀期間隱藏於大自然的密碼,然後轉化成文件與符號般的隱喻,在天目作品中以節奏與詩書寫。這是羅森豪的天眼通,藝術家的巫術與天目。
童年時廚房裡有個雙口大灶,羅森豪在母親炒菜時發現了一個個活現的精靈—火,它可以在黃昏的雲彩中發現他們的現身。負責看顧灶內火候的羅森豪,日復一日的學習,終於通曉了火的語言,他能辨識火的每一個片語跟句型,不同的火焰色彩代表的修辭與關係代名詞的各種強度語氣。
羅森豪以火的語言為基礎,逐步掌握了大自然的形形色色的對話,更在大自然的教養下學得了詩的文法。他傾聽大屯溪的吐納,樹林的韻腳以及春櫻的冷豔,從安山岩裡看到數百萬年前的煙火。在我們面前寂靜而冷凝的原野山林,對他而言是眾聲喧嘩的節慶,當中有他可以一一辨識的無數個親切向他問候的朋友。每一棵樹,每一朵花,每一塊岩石以及天邊的每一朵雲彩,都向他低吟私密的心緒,或者齊唱交響的旋律。他把這些朋友的歌紀錄成一首一首的詩與散文,這些就是他每一個燒成的天目碗。在羅森豪的創作裡,天目從一個建盞或吉州窯,乃至安土桃山時期的日本茶道般的異國情調,變成親切如我們自己土地的詩篇。
感官知覺的認識論從來不是線性純粹的,它永遠是多重面向與多重層次交錯綻放的。這是一種親身的修辭學,就像火的書寫一般,藝術家這樣形容:「火是一切物質當中最精緻的東西,你始終無法找到火光的空隙,也永遠留不住,關不著她的熱力,它是一切的主角,而非中間介質,所以火可以轉化各種物質。」「有千變的火舌就有萬化的釉色。」(《微塵液相》)
受到精彩的色形感染,許多藝術家都嘗試去製作天目陶器,多數在釉料下工夫,在火候的控制上鑽研,並且在窯變的豐富上耽溺。然而模仿天目的色與形,事實上一直是一種表相的同一性,彷彿是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的表相法則。羅森豪則進一步把心思放在胎土材料與釉料的靈魂上,他們在原來的大自然中富含的精氣與靈性。他不刻意尋求工廠製造販售的制式既成的含鐵釉料—那種被純碎化與理性客體化分析抽象般的材料,而是從大自然中以及藝術家生活的泥土裡找出鐵的成分—活生生的充滿生命動力與回憶能量的含鐵土壤,於是在使用這些材料的同時,也一併召喚了其周邊的每一個泥土在時間之中的生命經驗與記憶的痕跡。如此的動機與創作,賦予了作品強烈的差異性動能,讓所有羅森豪的天目在每一個細節與整體呈現全然不同於其它的天目作品。這是羅森豪最特殊的能力,他擅長追尋到事物最原初的本質,進而總體重新創造,一種由本質原點出發的創新與改造,彷彿土地母體般的生命創造動力與能量。
非親身化→親身化→輪迴
體會到成住壞空的智慧與真理,才有生生不息的循環動能,進而把握其中每一個瞬間的美好。
羅森豪的天目不只是一種創造(creation)更是一種生命動能(procreation),一種深具天地自然的生命動能的創造生產;是生命的實踐同時也是哲學的思辨,一種生命最基礎的本質實踐的哲學。他總是在作品中直抵自然本質的核心,在輪迴轉化的過程中,從自然,從泥土,從火光瞬息綻放的能量與精采。在他的天目碗溫潤的觸感與折射的光澤中我們閱讀到土地的詩篇:沼平車站聖潔的櫻花、奮起湖微風中的草香、奇萊山偉大的岩石峭壁與雪山的圈谷、北海岸煙波上的晚霞與大屯山早晨的凝露。
在羅森豪的天目中,我看到了非親身化(desincarnation)的轉化與隱喻,也感受到了身體親身化(reincarnation),經由材料與作品的過渡與穩定,體認到成住壞空,苦寂滅道之後的開懷與自在,與每一個當下因緣的美妙靈動。
2017年以後的作品會移到網站喔!
6 年前